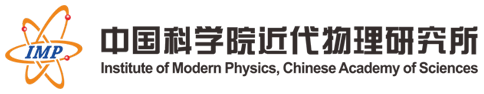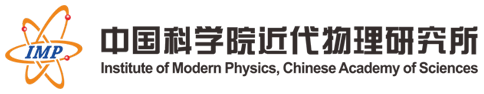大力支持基础研究正当时
文章来源: | 发布时间:2022-07-01
文章来源: | 发布时间:2022-07-01 | 【打印】 【关闭】
近日,财政部部长刘昆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提交的关于2021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显示,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科学研究的支持。报告表明,国家一方面重点增加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达720.91亿元、增长15.3%,并围绕扩大经费使用自主权、加强激励力度等7个方面出台了25条具体的政策举措。另一方面,针对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以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韧性为目标,加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并启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奖补政策等措施,可谓在绘制振兴我国科学研究的蓝图上又添加了一抹亮色。然而,从近几年各项经费支出的数据变化以及政策支持的方式和资金分配来看,可喜又可忧。可喜的是国家持续用实际行动表明了对科研的重视和推进的决心,而堪忧的是当下对科研的支持体系和机制的认知还较为模糊。尽管自2000年以来我国财政科研经费投入持续增加,金额规模也达到了世界数一数二的水平,但如果不进一步明确中长远发展目标,仅阶段性地调整对不同性质的科研支持的战略,有可能会错过换道发展的战略窗口期。科学研究按照其性质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其中,基础研究指的是基于研究者的科研好奇心和自由探索之精神,针对自然现象或观察到的事实提出假说,并进行理论探究和实验证明。其重点在于原发性和创造性,不关注商业价值和应用的即时性,在成果主义评价体系中也被称为“无用”的研究。而应用研究是利用基础研究所发现的新知识,确认其实际应用的可能性,并针对既有的应用方法进行改善和更新,重点聚焦于有效性和有用性;试验发展则是利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成果,并结合实际经验所获得的知识,探寻新材料,开发新设备、新产品、新工艺以及新的系统和服务,属于广义的应用研究,侧重于价值实现和收益性。比如,从国家发展战略出发,除了科学家好奇心驱动的、没有明确目的自由探索类的“纯粹基础研究”之外,也存在由国家和社会需求或科学前沿目标导向的定向性基础研究。后者在我国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在我们的语境中,也常常把“基础研究”和“研究基础”的概念混同使用。作为一个追赶型的新兴科技国家,我国进一步强化基础薄弱的学科,以及推进实验室等大型设备的基础配套,无疑是十分关键和必要的。然而,如果在统计政策性投入时不加以严格区分,在成果主义的评价体系下,科研基础设施的部分也会被计入基础研究的框架内,导致对基础研究投入和产出的过大评价,进而直接和间接地对“纯粹基础研究”产生挤出效应。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不存在所谓的先有基础研究而后有应用研究的线性关系。更多的是,先有一个应用目的和场景,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发现需要基本原理的支持,而在应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某些现象又可能会触发新认知的突破,即大多数的科技进步表现为“应用—基础—应用—基础”交互推进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基础研究对推动科技进步具有未雨绸缪和蓄水池的作用,或是相当于具有创造力的土壤环境。一个国家基础研究的多样化和积累是一国科技原创力和科技自立的磐石,如果没有长期持续的基础研究的积累,是无法萌芽新技术并推进技术进步的。从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的贡献来看,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也十分显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推算,专利作为应用研究的成果被引用的高峰期大约是在其公开发表后的第3年,而作为基础研究成果的科学论文的被引用高峰期则大约是在其发表的8年后,表现出基础研究对社会的影响面更大、时间更长。同时,如果一个国家的基础研究保持年均10%增幅的话,将带来劳动生产力0.3%的持续上升。然而,从我国政府经费支出情况看,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并不理想。首先是在2020年的全国科研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占比分别为6.0%、11.3%和82.7%,绝大部分用于试验发展,应用研究是基础研究的2倍左右。尽管对基础研究投入有持续增加的趋势,但仍然仅占总经费的5%~6%,与法美日英的约20%相比差距甚大。从企业、大学以及政府所属研究机构3个研究主体的经费支出结构来看,首先,我国企业的研究活动几乎全部属于试验发展范畴,有少量应用研究,基础研究甚少涉足。与之相对照的是,发达国家的企业也在积极开展应用研究和一定的基础研究,甚至诞生过企业研究人员获得诺贝尔奖的案例。其次是过去20年里大学的研究经费支出中,应用研究一直占据主要部分(约占50%~60%),试验发展从30%下降至10%左右,基础研究的占比从20%上升至40%,但仍远低于法国的80%、美国和日本的50%~60%。第三是政府所属研究机构的试验发展占比最大维持在60%以上,应用研究约为20%~30%,基础研究占比在过去20年里缓慢上升,约占10%。上述数据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延续着以技术改造为代表的科研支持倾向性,产官学的主要科研目标是为工业化和战略性产业发展服务的。因为自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来,借鉴和消化外来技术是科研的主要内容,也是历史的必然。在国际环境相对友好的前提下,利用全球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的资源禀赋状况,我国科研实力得到了快速提升。但相伴而来的则是对基础研究的认知变得模糊,支持力度相对较弱。近年来随着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科技竞争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一旦遇到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即刻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因此,强化基础研究、实现科技自立成为时代的呼声。如果说借鉴和消化外来技术是追赶型国家容易倚重应用研究的主要原因,那么要实现弯道超车的超越式发展,基础研究就将成为主动力。遵循“应用—基础—应用—基础”的发展轨迹,在取得大量应用成果的基础上,适时按下推进基础研究的按钮可以说是正当其时,尤其在日益严峻的内外部环境下,更是刻不容缓。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不能只停留在对竞争性科研经费的放管服,或对企业科研行为的奖补政策等微观层面,而是要站在可以俯瞰的高度,在真正理解基础研究,尤其是纯粹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的基础上。一方面,将市场可以有所作为的研发让给市场,发挥成果主义和商业价值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遵从基础研究的特质和发展规律,提供更多的非竞争性资源,形成一股不唯成果主义、可以自由畅想的探求真知的科研风气。如此,方能为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以及全人类的进步提供多样化的、具有原创力的知识积累,可谓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备注: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科学报,本文作者 袁堂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